北宋父子词人晏殊、晏几道,一直为后世读者所喜爱,但要论及他们二人谁更受欢迎一些,恐怕会沦为一个比较“是非的问题”,因为这纯属“个人看法”,所以争论起来毫无意义,且因各人性情、审美的不同导致这个问题很难有公允的答案。那么我们就来一个折中吧,我们试图从他们的词作中找出一些微妙的差异,看看他们二人在抒情上各自有着怎样的侧重,从而也可以使我们能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审美,了解我们喜欢一个词人到底喜欢他哪一点、钟情他哪一句。且来细读晏殊的一首《浣溪沙》
浣溪沙
北宋 晏殊
一向年光有限身,等闲离别易消魂。酒筵歌席莫辞频。
满目山河空念远,落花风雨更伤春。不如怜取眼前人。

上阙三句表明了一件事,词人在宴饮宾客。或许是有曾经的故人没来,又或许是词人一时感伤而叹起人生离别,不管怎么样,我们可以将这三句理解为一种“悲观愁绪”的表达。作为一个太平时期的富贵宰相,国家平安无事,自身荣华享之不尽,又是一个多情多才的文人,于是他常常会吐露出一些人生苦短、富贵荣华如过眼云烟似的愁绪。了解了词人的背景再来读这首词,就发现开篇第一句自有一种高境界。“一向年光有限身”,是说人的一生就如这一晌儿年光一样,倏忽而逝,短暂无常。这样的哲理似乎是每个人都能讲出来的,但到了晏殊这里不一样,有两点。一是,在大多数时代,身处宰相之位的人,并不是像他这样,大多数执掌权柄的人物,要么汲汲于永葆家族富贵,要么为国事日夜操劳,他们并不是富贵闲人。二是晏殊能细腻地感知到生活本质的无常与感伤,但他是愿意面对这些的,不仅愿意面对,而且要诗意地面对,这就是最大的不同。

既能细腻地感知,又能用诗的语言讲出来,这不仅得有才,还得有情,还得是个明白人,明白这些事物最终都是要消逝的,强求不来,不如顺其自然。
“等闲离别易消魂,酒筵歌席莫辞频。”化用江淹《别赋》中的名句“黯然销魂者,唯别而已矣”,不过相比于江淹赋中的生离死别,晏词中的离别显然更普世,更近于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情感。等闲,就是普通的、平凡的。词人说“等闲离别易消魂”,说我们生活中这种普通的、看似轻易的离别,更令人难过,这就很有“人间烟火”的意味了。我们可以将词中的“离别”理解为一种“欢愉时光的结束”,我自己常常就有这样一种感受,每次与同学朋友们聚会畅聊时,都是欢快的,但聚会结束后就立即生出一种无比落寞的情绪,萦绕心头无法排遣,有时甚至聚会还未结束就已开始伤感了(看来我也是古之伤心人之一呀),这或许也是“等闲离别易消魂”的一种吧。

《宋人轶事汇编》引《避暑录话》中记载,“晏元献(晏殊谥元献)喜宾客,盘馔皆不预办,客至旋营之。每有佳客必留,客前皆设一空案。宴饮既行,酒食渐至,歌乐相佐,谈笑其间。数行之后,案上已粲然矣。稍阑,即罢遣歌乐曰:‘汝曹呈艺已遍,吾当呈艺。’乃具笔札,相与赋诗,率以为常。前辈风流,未之有比。”这个典故或许可以用来解释上阙最后一句“酒筵歌席莫辞频”了,也说明了晏殊正是那种“认清生活的本质后仍然热爱生活”的人。他不是刻意地安排什么行乐之事,而是一种既来之则安之,既安之则享之的人生态度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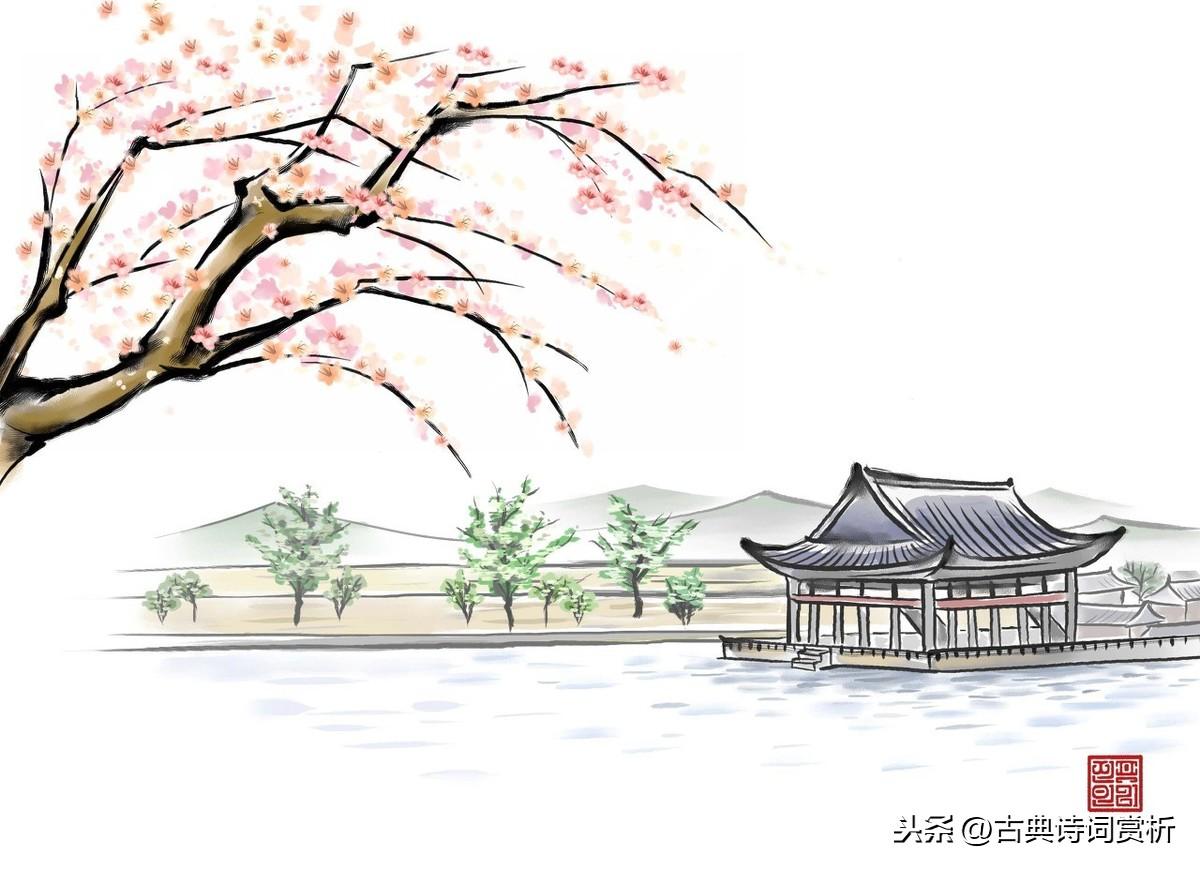
词转下阙,“满目山河空念远,落花风雨更伤春。不如怜取眼前人。”满眼望去,山河壮美,激荡胸怀,却陡然升起思念远人的伤感;落花时节,风雨尤厉,伤逝的愁绪更令人憔悴。不如好好儿珍惜眼前陪伴着的人吧。这三句有一个转折,词人从一种伤逝的愁绪中找到了一个解脱的方法,即珍惜眼前可以拥有的、能够抓住的。因为前两句已经很“空”很“伤”了,再往下写就容易往颓废的人生观上靠拢,而晏殊显然不会。也或者他是为自己内心细腻易感的情绪找到了一种诗意的妥协,身为一个富贵宰相,他在人生成长中必然会有积极进取的一面,而另外一方面作为一个多情文人,他又是容易感伤的,那么怎么办呢,面对自己内心的这一对矛盾,词人选择向两边都妥协,而他妥协的方法,就是珍惜眼前拥有的,并歌颂她们。

“满目山河空念远,落花风雨更伤春”,这两句极致的伤怀抒情很容易让你想到晏几道,因为与他的词风很像,但不同就不同在第三句,若是让晏几道来写,就有可能写成一种如泣如诉式的伤情,比如晏几道词中最常用的两个逃避现实的字,“梦”和“醉”,“梦后楼台高锁,酒醒帘幕低垂”、“今宵剩把银釭照,犹恐相逢是梦中”等等。但晏殊就是往回拉,他也感伤,但最终还是会回到眼前的美好上面。
从下阙这三句的安排上,我们可以窥探出晏殊与其子晏几道在词风上的微妙差异,我们可以用“伤感”这个词的两面来解读,即晏殊词在抒情时更侧重于“感”,他的词无论是表达对美好时光难以常在的慨叹,还是离别、怀念情绪的抒发,都只是将自己内心的愁绪抒发出来而已,最终还是会回归美好和诗意。而晏几道则侧重于“伤”,不过他也是真伤,命运的不同在这父子二人身上找到了完美的样本,一个低开高走,一个高开低走,这也就导致了他们二人在文学艺术的诠释上,有了一种微妙的、大类相似实则不同的区别,不过即使是有区别,也是诗意的。


